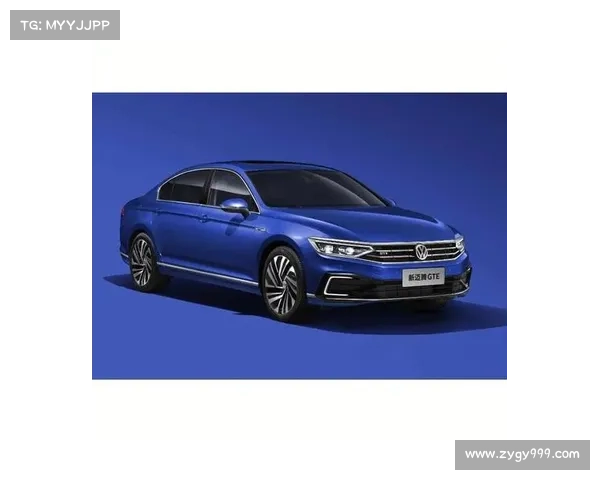计划经济年代的最后一个十年,城市居民的生活在方寸之间展开。1970年至1980年的中国城市,粮票比钞票金贵,空间比时间稀缺。

人们挤在狭窄的弄堂里或筒子楼中,在物资短缺的背景下,用朴素智慧经营着充满烟火气的生活。
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,13平米的单间里塞满了一个家庭的全部生活

。一张双人床、几件必备家具,孩子跟父母挤在一张床上,读书写字只能在小凳和折叠椅凑成的“学习角”完成。不足两米宽的内走廊成了公用厨房,两边堆满了煤球和生炉子的柴火,墙壁被烟熏得漆黑。

这样的场景遍布全国城市。在上海弄堂里,清晨是被生炉子的烟雾唤醒的。男人把煤球炉放在风口,熟练地引燃柴火,烟雾在狭窄的巷道里弥漫。主妇们拎着马桶走向公共厕所,开始一天的忙碌。没有独立卫生设施的年代,
住房的拥挤催生了独特的公共生活。夏天傍晚,竹榻藤椅占据了弄堂里所有有穿堂风的位置。男女老少摇着蒲扇,端一壶凉茶,在路灯下吹牛聊天,直到夜深露重才回家。这种被称作“乘风凉”的夏夜聚会,是酷暑中最惬意的时光。

那个年代,吃饭是件需要精打细算的大事。在太原市五一路,1972年初开业的昼夜便民粮店成了城市一景。国营粮店通常早上8点开门晚上6点关门,许多白天没时间买粮的市民只能干着急。粮店主任陈如碧向上级申请夜间营业,解决了职工们的燃眉之急。
月初的粮店总是排起长龙。凭粮本、粮票购买供应粮是每个家庭的月度大事。由于按人口、年龄、工种定量供应,家里有半大小子的,常常不到月底面袋就见底了。太钢、北营地区的居民甚至会骑车十几里,连夜来五一路粮店买粮。
粮票的珍贵在饭店里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揣着十块钱下馆子看似“阔绰”——炒肉丝六毛五一盘,烩面六毛一碗,十块钱足够点上好几道硬菜。但**没有粮票,多数时候只能干瞪眼**。买个五分钱的馒头还得交二两粮票,少数不收粮票的高档饭店价格要贵上一倍。黄昏是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。锅碗瓢盆的叮当声此起彼伏,嫂子们高亢的嗓音在走廊里回荡:“菊香,有生姜吗?”“芳姐,匀点葱我。”谁家做了好菜,必定分给左邻右舍尝鲜。王嫂烧一大碗干茄子

,李嫂蒸上米粉拌豆角,大嗓门刘望娣切了西瓜挨家挨户送。
在武汉的汽车制造厂单身宿舍,四楼的中年单身汉每次上楼都要故意绕道三楼走廊,哼着楚剧名段。被嫂子们截住时,他就像个孩子般乖乖立在那里唱起《三世仇》。另一个爱“装博学”的单身汉胸前永远挂着两支钢笔,腋下夹着厚书,被工友们戏称为“高博士”。他修电灯、收音机的手艺,成了在拥挤空间里赢得尊重的资本。
对门的丁嫂常常把三岁的儿子灵灵塞给单身的邻居。新裤子打扁,旧衣服钉扣子,都找她帮忙。灵灵稚声稚气地把“为了母亲的微笑”唱成“肥了母亲的微笑”,总能逗得大家开怀大笑。
购物是那个年代充满仪式感的大事。

西昌的工农兵商场是当时最大的综合性国营商店,3899平方米的建筑面积、两楼一底的钢筋混凝土结构,经营着百货、针织、五金等各类商品。
过年前的商场总是格外拥挤,人们背着背篓置办年货,满载而归。售货员站在玻璃柜台后,衣着朴素,发髻挽得一丝不苟。他们不够热情,但业务熟练——打算盘结账的手艺是必备技能。
商品种类虽少,质量却出奇地扎实。一个橡胶热水袋能用好几年,表面纹路清晰可见,塞子打磨得光滑平整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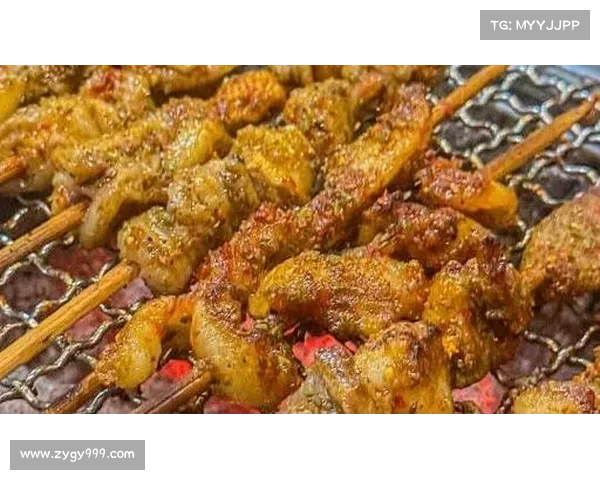
在天津,
八十年代的食品街人潮如流,自行车是最主要的代步工具。飞鸽牌和永久牌自行车最受欢迎,无轨电车则是公共交通的主力。路上基本不会堵车,老津门的百姓质朴无华,路上遇见熟人总要驻足唠上一会儿。

1992年底,粮价放开,票证取消,超市和个体粮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。太原市那间温暖无数人的昼夜粮店完成了历史使命,在老太原人的生活中留下美好回忆。筒子楼里的住户陆续搬进集资房或商品房,老邻居们起初羡慕那些住进高楼的人,后来却庆幸留在老宅能享受群居的快乐。

真实地烙下了一个时代的印迹。当现代人享受着物质丰富的便利,回望那个拥挤而温暖的年代,或许会感慨:空间可以丈量生活,却无法.丈量人与人之间的温度。在十三平米的单间里,在一根油条四分的日子里,在排队买粮的长龙中,生活以最朴素的方式展现出它最真实的质地。